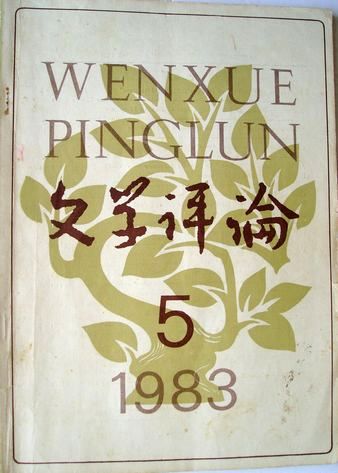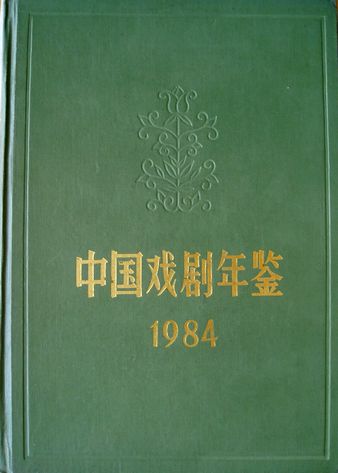太原岁月的时空4-----------郑波光(厦门)高五组【校友文萃】
|
太原岁月的时空4 历史剧理论探讨重要成果 作为高等学校的教员,我当时的理解,除了教学,最重要的是结合教学专业的科研,最好是带前沿性的科研。可以说我在《文学评论》发表三篇文章——王蒙、历史剧、赵树理,都是在当代文学专业范畴当中,而且都是当时的学术前沿。 我在太原师专开的是当代文学课程。王蒙当时是小说创作现代主义艺术手法探索的先行者,他的艺术探索遭受争议、质疑,他差不多处在风口浪尖上,我的《王蒙艺术追求初探》,算是对小说探索的支持,这是当时当代文学的热点。这是我在《文学评论》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我在《文学评论》发表的第二篇文章是关于历史剧理论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历史剧创作也是热点,陈白尘的《大风歌》,曹禺的《王昭君》,还有许多年轻作者的历史剧创作,如颜海平的《秦王李世民》,李民生、杨志平的《唐太宗与魏征》,黄志龙、次仁多吉、洛桑次仁的《松赞干布》等,重新引起60年代已经有过的关于历史剧理论的讨论,就是著名历史学者吴晗“历史剧是艺术,也是历史”,文学评论家李希凡“历史剧是艺术,不是历史”,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80年代关于历史剧的讨论,虽然热烈,但是都是在炒冷饭,翻来覆去全是60年代反复引用的欧洲17、18、19世纪的观点,跳不出欧洲古人的窠臼。我到山西省图书馆查阅所能查到的资料,我发现,西欧没有认真的历史剧理论,只有悲剧理论,他们拿悲剧理论来套历史剧理论。悲剧常常以历史为题材,但是对历史真实却没有要求,甚至违反历史都被允许。所以,在讨论中,颠三倒四,振振有词,却不能自圆其说。我以为都是西欧古代悲剧理论对历史剧的简单化套用,带来的恶果。因此,我提出: “悲剧要求历史服从艺术 我明确把对历史的要求,作为区别历史剧和悲剧的鲜明标志,并且把这两句话作为题头语,突出的放在文章标题下面,十分醒目。我论文的题目是《试论史剧理论与悲剧理论的区别》。发表在《文学评论》1983年5期。字数16600字。一万六千六百字。这是《中国戏剧年鉴》(1984卷)郑重统计的数字。可以算是重头的文章了。其实我原稿是三万字。被砍掉一半。留下的是历史剧的基本理论部分。砍掉的是《吴晗、茅盾在史剧理论建设上的贡献》。不过,我在这篇长文的末尾,留下一段重要的话,弥补这个遗憾: “吴晗最大的贡献还在于他在历史剧理论上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提出历史的要求,从而使史剧理论跳出悲剧理论的圈子,而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理论体系。由于西欧没有认真的史剧理论,因此,中国的史剧理论是开创性的。应该说,近数十年来,我国文学理论建设性的东西是不多的,如果我们能在六十年代所建树的史剧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研究,不断将理论探讨引深,那么,我国将能以一套比较完满的史剧理论瑰宝,去丰富世界文学理论的宝库,以填补西欧艺术理论中的一个空缺,作出我们独特的贡献。”(该期第71页) 我年轻时代有一种学术的雄心,从这段话中可以明显看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不断地折腾,中国文学理论不断破坏,建设性的东西很少。我真希望西欧缺少的历史剧理论,由我国去填补,所以,我对吴晗,茅盾在这方面的理论见地,特别赞赏。可惜这个课题,我没有坚持做下去,没有写成著作。正像钱钟书在创作《围城》后,本来要创作《百合心》,后来没有做,年纪大了以后,心就淡了下来。实在遗憾。 在这篇文章中,我有不少历史剧具体理论的探索,时间已经过去近三十年,令人欣慰的是,我的一些观点,已经被历史剧评论文章所运用。如历史剧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都离不开历史,这就是说,历史剧就是把历史变为艺术的功夫。这种功夫,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把历史人物性格化,二是把历史事件戏剧化,这是史剧作者将历史变为戏剧的两个基本功。”(该期第64页)当然,只有郑重的历史剧作者才关注历史剧理论。不过,不管时代任何变幻莫测,任何时代总还是有郑重的历史剧作者的。 我在《文学评论》发表的文章,很荣幸都得到学术界关注。 1982年的《王蒙艺术追求初探》发表后,人民日报《文摘报》1982年2月9日5版介绍,当时是太原师专中文系杜丕璋老先生告诉我,并且把他订的这张报纸送给我,我很感激他,我至今保留着。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主办的《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3期动态栏目以“王蒙小说的艺术结构”为题选登我文章“心理结构和情节结构”第二部分全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82年2期全文复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王蒙专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出版)全文选入)。当时算是一炮打响。 1983年《试论理论史剧理论与悲剧理论的区别》发表后,人民日报《文摘报》1983年9月30日5版介绍,中国人民大学《戏剧研究》1983年9期全文复印。戏剧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中国戏剧年鉴》1984卷第408页,在《历史剧讨论的发展与深化》一文中,专门一段写道: “郑波光主张对历史剧概念的理解应该严格(《试论史剧理论与悲剧理论的区别》《文学评论》1983年第5期,详见单篇文摘)。” 在该《中国戏剧年鉴》第370-371页,每个页码2500字,共5000字,末尾注明“(茹辛摘辑,原文16600字)”,可见相当郑重其事。 这部《中国戏剧年鉴》是1991年5月15日我和夫人在太原工人文化宫游书市,意外发现的,真是喜出望外。这是我的太原岁月的时空,一件难以忘怀的快事。 关于这篇文章,更加让我高兴更加欣慰的是,我的历史剧理论的观点,已经载入史册。这就是古远清先生的《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下两册,台湾文史哲出版社中华民国八十八年四月初版,应该是1999年4月出版。在下册第六编第二章“热门话题”第六节“历史剧讨论的发展与深化”(此标题跟上边《中国戏剧年鉴》完全一样),这一节就是从介绍评述我的论文观点开始的: “文革前流行的历史剧观点是:‘历史剧是文艺创作’,因此‘历史剧是艺术,不是历史’(李希凡)。这种观点近年被郑波光提出根本性的否定,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犯了‘把悲剧理论简单地套在史剧理论上’的错误。须知,悲剧与史剧对历史的要求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悲剧要求历史服从艺术,史剧要求艺术服从历史’,悲剧‘对历史却无需严格要求,甚至可以完全违背历史’。(郑波光)至于吴晗说的‘历史剧是艺术,也是历史’(吴晗)郑波光认为它正确地解决了历史剧中历史与艺术的关系,是历史剧这种艺术形式的特点最完满的概括。……(郑波光)”(该书下册第653页,654页也有一处引到我的观点)。 显然,该《理论批评史》的著作者,把我作为新时期“历史剧讨论的发展与深化”的突出代表。我内心充满感激。上世纪在海南岛开会,我遇到古远清先生,跟他合影,这里登一张合影照片。向他表示感谢和敬意。 2012•7•10•厦门前埔 |
|
|
|
| (1) 《文学评论》1983年5期 | (2) 《中国戏剧年鉴》1984卷 |

(3) 郑波光、古远清1996年在海南岛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