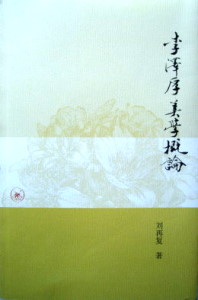真理的美声永恒------------郑波光(厦门)高五组【校友文萃】
|
真理的美声永恒 真理的美声永恒 李泽厚堪称
|
|||||||||
| 2009年12月23日,我收到北京三联书店寄来2009年12月刚刚出版的刘再复同学的新着《李泽厚美学概论》,我打电话给一样的大学同班同学林兴宅,他说也收到。这次跟2006年10月同样是三联出版的《红楼梦悟》,用手写的“刘再复先生赠书,三联书店代转”不同,是在信封上直接用电子打印“刘再复赠书”标明。看来荣幸得到赠书的人不少。
收到此书后,当时就读了一部分,感觉相当不错:此书不但比较简明清晰概括李泽厚建构的独一无二的中华美学体系,而且涉及文史哲广泛领域,可以说是当今一件层次颇高的精神盛事。我告知贵州大学文学院的好友徐明德教授,(文化学者。着有《鲁迅文化心理结构解析》等着)徐兄特别赞赏李泽厚和刘再复两位先生。嘱我读完寄给他一阅。因为我读书很慢,儿子发现可以网上购书,网上有此书,我便购了此书寄送他一部。他非常喜欢,十分赞赏,回信说:“再复先生对李泽厚美学体系的总结,很好,恰到好处,又不冗繁,说得很明快。”除了徐兄,我还购一部此书赠送集美大学原副校长、厦门电视台曾专门报道介绍过的厦门著名藏书家商振泰校长收藏。(鲁迅研究学者,策划合作着有《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我特别感激商校长的是,1996年我在集美大学中文系主任任职期间,因为中文系资料室图书太少,他特批三万元给中文系购买图书,我组织各教研室到书店购买一大批中文专业图书。现在集美大学文学院资料室使用的不少重要图书(如《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全套数十本,《王国维遗书》(全十册)等)就是当年购置的。我一直心存感激。这是题外话。 1996年,刘再复在《回望二十世纪中国》中郑重评价李泽厚为“中国人文科学领域中的第一小提琴手”,在本书《李泽厚美学概论》中,他坚持这一看法,惺惺相惜,由衷赞叹。在本书自序中,开宗明义,醒目写道——“自序: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小提琴手”。李泽厚是极富原创能力的当代中国哲学家、美学家、思想家。刘再复评价,并无溢美。 当今人文科学,乏善可陈。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创新能力下降,这已是社会共识。因此,现在处处在呼唤创新精神,这是一种好的现象,好的趋向。现在许多出版社再版和出版不少上世纪和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富有原创性的名著和新着。重视中国原创学术真理的传承和传播,是弘扬中华新文化的大好事,令人高兴和欣慰。真理就像杰出的小提琴手演奏出来的美声,其美与美感是客观存在的,真理是永恒的、不朽的。应该说,国人对李泽厚先生、刘再复先生还是十分敬重的。他们的书的频频出版和畅销,就是证明。 李泽厚先生今年已经80岁了。本书扉页对李泽厚是这样介绍的: 李泽厚 1930年生,湖南长沙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德国蒂宾根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和哲学、美学研究。著述甚丰。 他的著作,最重要的有《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79), “三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华夏美学》(香港三联书店1988)、《美学四讲》(香港三联书店1989),《回望二十世纪中国》(与刘再复合着,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6),《历史本体论》(北京三联书店2002),《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北京三联书店2005),《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等。(详见本书252页“李泽厚著作年表”) 李泽厚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人文科学家,在人文科学领域,影响是巨大的、全方位的。刘再复称他是“中国人文科学领域中的第一小提琴手”,他是当之无愧的。 这里我先来讲一个旁证。1999年(中华民国88年)4月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版的古远清着《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下两册),上册第二编第一章第四节“李泽厚探讨美的历程”,对李泽厚有比较全面的介绍和相当高、相当中肯的评价,可以作为本书刘再复评价的一个佐证。他认为,李泽厚是50年代中期美学论争中“腾空升起的一颗新星”,他“确立了一个新学派,他本人也成了和朱光潜、蔡仪这些美学前辈不同时代的代表人物。”在这一节的最后一段,大有总结和总体评价的意味,这样写道: “李泽厚新时期以来使用的一些美学概念和命题如‘主体性’、‘心理本体’、‘积淀’,一时间被学术界许多学者共同使用。尤其是‘主体性’的概念在刘再复与陈涌、姚雪垠的论争中,被一些论者作为文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词汇使用,致使一些人称李泽厚为学术界的‘思想库’,而他的美学思想,在八十年代便占有了主流的地位。当然,李泽厚在新时期影响学术界的不限于美学,还有涉及文史哲领域的思想史论稿和哲学专着。这些论着与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思潮相互呼应和补充。这些新思潮新在与流行看法采取修正乃至对立的态度。李泽厚的观点和主张不仅集新思潮之大成,而且还给新思潮的弄潮儿提供理论依据。……”(173页) 这里提到李泽厚被称为学术界的思想库,他所使用的和原创的(最著名的有“积淀”等词)词汇已被作为文艺现代化重要的词汇使用,他的美学思想在新时期占有主流地位,他的影响超出美学,涉及文史哲广泛领域,他的观点、主张,集新思潮之大成,成为新思潮的理论依据。这一切,无不证明刘再复1996年提出的论断是可以成立的——李泽厚确实堪称“中国人文科学领域中的第一小提琴手”。 比较起来,刘再复的学术专着《李泽厚美学概论》,是更为学理,更为系统、全面、深入,更为提升地阐述、论证自己对李泽厚学术地位和贡献的论断——“中国人文科学领域中的第一小提琴手”。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全书的目录框架: 主篇 李泽厚美学概论(2006——2009) 李泽厚与中国现代美的历程(1991) 副篇 与李泽厚的美学对谈录(2008) 相关的哲学、历史、艺术思考——与李泽厚对谈选编 一、 走出语言学世纪(2006) 附录 李泽厚:关于“美育代宗教”的杂谈答问(2008) 后记 全书目录非常清晰:“主篇”是美学;“副篇”、“附录”涉及文史哲等广泛人文科学领域。 对于这部著作,本书封底有一段相当全面精辟的概括和评述。这样写道: “本书是在1990年、2006年的两次讲座基础上进行学术性提升后的结果,概说了李泽厚美学富有原创性与体系性的品格,更说明了这是拥有哲学-历史纵深度的追根溯源的‘男人美学’,而非尼采所嘲讽的局限于艺术鉴赏的‘女人美学’。书中还揭示了李泽厚美学的双向架构:向外打通马克思与康德而创造了人类学主体实践美学;向内打通儒、道、屈、禅而创造了中国美学研究的双壁《美的历程》与《华夏美学》。尤其是《美的历程》一书,更是全然首创的中国审美趣味变迁史(而非艺术史)。作者对李氏著述和思想烂熟于心,在本书中,李泽厚所有的美学理论硬核均被作者用以轻驭重的感受性语言所化解和阐释。” 确实如此。李泽厚美学,本书概括了三个鲜明特点:原创性、体系性、哲学-历史纵深度。这三个特点顺序由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分别阐述。在第二节“李泽厚美学体系图式”中,作者还详细列出两个图表:(一)美学概论,包括一、“美的哲学”(人类学本体论美学)、二、“审美心理学”(美感发生学)、三、“艺术社会学”(审美形态学)。这三部分,每一部分又层层细分为许多层次。(二)“中国美学史论”,大的分“经”、“史”两部分,每部分也同样层层往下细分。可以看到,刘再复驾轻就熟,阐释、辨析得十分精细。由于自己浅学,我读此着,不只是温习旧识,更多的是学习新知。 刘再复认为 李泽厚美学是“真正的原创性美学”,与西方最大的不同,是在“上帝缺席条件下的中国现代美学,是无神论的美学,最后又是把审美视为高于宗教并替代宗教的美学。”(6页)书中多处印证这一观点。在第七节“中国古代美学的现代阐释与‘情感真理’的发现”这一节中,写到“李泽厚把中国美学概括为四大特征”,一、“以乐为中心”,二、“线的艺术”,三、“情理交融”,四、“天人合一”。下面有刘再复的一段阐释和发挥,我以为相当精彩,抄录如下: “中国数千年的文化,数千年的文学艺术,李泽厚能作此概述,而且击中要害,实在难得。尤其是第一特征(乐为中心),更是贯穿于他的美学系统中。关于‘乐感文化’,我把他的大量论述概括为以下四个要点:其一,肯定此生此世的价值,肯定生的快乐。不是生而有罪(基督教),不是生而悲苦(佛),不是生而有错(老子:‘大患’),而是生而有趣。用李泽厚的话说,不以另一个超验世界为指归,他肯定人生为本体,以身心幸福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为理想、为目的。即使在黑暗和灾难年代,也相信“否极泰来”,前途光明,这光明不在天国,而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其二,确认生命价值在于生命本身的奋斗和进取,即在于用乐观的态度去争取未来,天行健,人亦行健,人生不是仰仗外力不是仰仗上帝的肩膀,而是君子自强不息。其三,确认生命最高的乐趣在于情感的快乐,而不是物欲的快乐也不是道德的快乐,换句话说,在中国礼乐系统中,处于最高地位的乐,其核心意思是同天地和谐的情感愉悦。‘乐感文化’是‘情本体’文化,不是‘理本体’文化。其四,‘乐’不是盲目乐观,是正视忧患又超越忧患的快乐,进而又是感到与宇宙、自然和谐共生的至乐。忧患中有悲凉感,但少有绝望感。”(重点黑体字为引者标明) 关于李泽厚的“乐感文化”,刘再复概括的“四个要点”,清晰而透彻。其中就强调了中国美学的特点是上帝缺席的美学, “人生不是仰仗外力不是仰仗上帝的肩膀,而是君子自强不息。”这就是说, 中华民族自信、自强,只靠自己的力量,不靠外力,不靠上帝,这就意味着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坚毅最顽强的民族。 作者认为,“乐感文化”“以乐为中心”,还不是李泽厚中国美学研究“最后最重要的贡献”,他以为最重要的贡献是,他晚年在中国文化、中国美学研究中,发现了两大真理:“一是‘巫史传统’,这是中国文化的本源真理;二是‘情本体’,这是中国文化的情感真理。”作者还以激赏的口吻写道:“一生奉行理性主义的李泽厚最后喊出‘情感万岁’的口号,这是他发现情感真理后的‘至乐’。”(以上三处引文均是第56页) 此书内容极为丰富,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我读此书,有两点比较深刻的印象。下面我就谈谈这两点印象,也可以说是读此书的两大收获。 第一点,“情本体”。“情本体”确实是李泽厚晚年发现的至为重要的中国文化真理和哲学真理。这是发现,也是肯定。它不仅超越中国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这种残忍愚蠢的“理本体”,而且超越西方只认“理”不认“情”的“理本体”。在《副篇》的《与李泽厚的美学对谈录》中,刘再复说到李泽厚曾说“西方只讲‘合理’,中国则不仅讲‘合理’,而且还讲‘合情’。‘大义灭亲’,中国人很难做到,因为它合理但不合情。”(103页)尽管他们两位都知道,中国人讲“合情”,重人情,容易产生弊病,如“虚伪”,“走后门”“拉关系”,但是他们却一致肯定“情本体”使中国人的人际之间“更为密切也更为温馨”。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国家,一个很有亲和力的国家。这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国人的骄傲。这一点,李泽厚、刘再复从美学,从文化哲学的高度上,从正面加以肯定。 这就是此书给我留下的第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情本体”的价值和意义。 第二点,“乐感文化”。这是我读此书更重要的一点心得。关于“乐感文化”,刘再复概括的四点(见上面引文),尤其是第一、第二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它让我们重新思考、重新发现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的,我们中华民族性格的光明面、优长面。 20世纪五四前后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一代学者的“批判国民劣根性”,林语堂关于国民性的学术专着《吾国与吾民》,当时的时代大潮,主要关注的无不是中华民族性格的负面、阴暗面。新时期以后,“劣根性”挖掘似乎更加变本加厉。“劣根性”差不多成了中国民族性的代名词,令人压抑和沮丧。当然,民族劣根性的一面,永远值得我们关注、批判和改造。但是,我们民族除了“劣根”需要改造,难道没有“优根”的一面,值得我们发掘和发扬?此书让我特别欣喜的是,通过刘再复对李泽厚的“乐感文化”的郑重阐释,我第一次高兴地发现中华民族性格的优良根系,这就是中国人,(刘再复阐释)一,“肯定此生此世的价值,,肯定生的快乐”,中国人不靠虚无缥缈的宗教, “即使在黑暗和灾难年代,也相信‘否极泰来’,前途光明”;二,“确认生命价值在于生命本身的奋斗和进取”“ 用乐观的态度去争取未来,天行健,人亦行健,人生不是仰仗外力不是仰仗上帝的肩膀,而是君子自强不息。”在《对谈录》中,刘再复还补充说:“乐感文化实际上是困境中的一种积极精神、悲苦中的一种不屈不饶。”(103页) 从历史看,中华民族确实灾难深重,但是从古至今,不屈不饶,顽强生存下来,而且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实在令人惊叹! 中国民间拥有大量在困境中表达乐观的成语、俗语、谚语: 天无绝人之路 这是中国人劝说人们在困境面前要想得开的普通话语,但是这些话语包含着中国人普遍的信念和心态,这就是克服眼前困难,渡过人生难关,前途总会光明的信念。也就是“否极泰来”,“否极”之后必然会有“泰来”的坚定信念。对个人是如此,对国家,对民族,对世界,对人类,也是如此。中国人永远不会失去希望。 李泽厚原创、刘再复阐释的“乐感文化”,让我们不光是情感的,而且是理性地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坚毅、最顽强、最自信、最乐观的民族,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阳光的民族。过去,我们用“勤劳勇敢”来界定我们中华民族,一点都没有错。从李泽厚、刘再复的发掘和阐释,“勇敢”一词是完全可以涵盖“坚毅、顽强、自信、乐观、阳光”这五个词的内容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以为,李泽厚、刘再复给我们一个新的信念——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阳光的民族! 2009•12•23——2010•5•23厦门前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