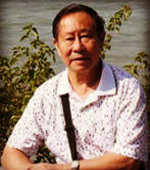张时贤校友、陈榕先生之访谈录(一)【校友风采】
|
世间没有一种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可以不经过艰辛和勤奋劳动而得到。——美国•爱迪生 |
漫漫人生路 无悔笑黄昏
——访谈录之一
|
|
陈: |
有一句谚语说一个智慧的老人就是一座图书馆,虽然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不断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是人性中最本质的部分构成人类社会最稳定的传统,而这些传统全靠有心的老人一代又一代持续传承,在生活中常常发现民族传统的积淀往往和老人丰富的经历融合成一体,我认为您就是这样一位弘扬传统的睿智老人,因此这次访谈是否可以先围绕您的个人经历谈一谈? |
| 张: |
好的。不过你将我送上自己从未企求过的高度了。我认为自己的人生历程极其普通、平凡,本不值一谈。但是正因为普通、平凡,我的一些感悟,对我所爱和爱我的亲友,也许有一些参考的价值。因此,愿意对你提出的一些问题作简单回答,不妥之处,请谅解。 |
|
|
|
| 陈: |
您过谦了,传统其实就体现在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民间有句老话:“三岁看八岁,八岁看到老。”这说明一个人早期养成的习惯和树立的价值观对其一生的决定性影响。因此,我首先感兴趣的是您反复强调国光中学对您的塑造和培养,是否可以说在国光中学的求学经历奠定您精神世界的基础? |
| 张: |
我于侨界楷模李光前先生创办的南安国光中学所度过四年美好的学习时光,在《芙蓉网》上发表的《岁月悠悠情未了》一文中已有详尽的叙述,就不用再重复了。 |
|
|
|
| 陈: |
如今的学校和学生与您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了。我所在的私立高中招收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闽北各乡镇,家境并不宽裕,有的甚至困难到毕业时都无法缴清学费,但是从他们中一些人身上我看不到艰苦奋斗的作风,不仅在吃穿玩乐方面的开销与城市普通家庭的孩子差不多,而且竟然会责怪父母挣的钱不够他们用;不仅逃避每个人都必须参与的教室和卫生区的值日,而且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还不如城市的孩子。他们的表现真是令人震惊,为什么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把节俭的美德“扔到太平洋里去了”?我注意到您近来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回忆文章,侧重于怀念先人故交和弘扬传统文化,这是否表明您对下一代的思想认识和人生发展有了某种程度的担忧? |
| 张: |
不!我对新生一代是充满信心的,他们的开拓创新精神和敢为人先的气魄,以及努力掌握现代科学知识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都是祖国和平崛起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宝贵财富。 |
|
|
|
| 陈: |
我认为应试教育也引发一种特别让人担忧的现象,就是把知识当作升学的垫脚石和敲门砖,达到目的后便弃之不用。在越来越重视专业化的当代社会,如果没有长期的积累是不容易出成绩的。您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一些突出的成果,而您却是学工科出身,我特别想知道您是否根据自己的兴趣转行搞社会科学? |
| 张: |
不要说在提倡作一枚小小螺丝钉的那个年代,就是在大力宣扬个性彰显的当今社会,想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工作也是很难实现的奢望。在当时大力发展工业的大背景下,我踌躇满志准备将所学的专业知识应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中,政治理论工作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的转行是由党组织决定的。在那个“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的年代,国家干部的工作是由上级组织安排的,个人并没有自主择业权,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分配,这是不可违抗的铁则。 |
|
|
|
| 陈: |
您刚参加工作没多久,不仅专业方面遭遇突变,而且生活方面也遭遇突变,那就是“三年自然灾害”。几乎所有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们,在谈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无不心有余悸。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您一定吃了许多苦,能否详细谈谈您当时的具体情况? |
| 张: |
我刚走上工作岗位,就遇到“三年自然灾害”。 |
|
|
|
| 陈: |
您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苦多乐少的经历,对您后来的消费观念是否产生很大影响?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因为前面您提到当时教师地位很低,主要体现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很低。如今教师的各种待遇皆有所提高,我知道您的退休金并不菲薄,可您依旧住在学校二十几年前盖的小居室套房,家具和电器也没有与时俱进,让我觉得您亏待了自己。现在许多年轻人认为大多数的老年人对自己太抠了,这是否与他们曾长期生活在短缺经济时代,特别是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有关? |
| 张: |
我们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确实生活过得极其艰难,但对我们后来的消费观念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
|
|
|
| 陈: |
我虽然有幸没有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可一直以来对与此有关的问题非常关注,因此还想与您进一步探讨。我国幅员辽阔,多种气候类型共存,每年都有可能发生各种或大或小的自然灾害,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仅在“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1960年)就饿死一千多万人,因此学术界有一种观点渐成主流,那就是认为“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人祸,您能否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专业知识,以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谈谈对此的看法? |
| 张: |
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人祸”的观点,我认为不完全准确。我的观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所谓“人祸”,就是党在工作中的失误。自1960年开始,突然出现这么严重的困难局面,过去总是归咎于或者主要归咎于自然灾害,不敢从主观上和从领导的决策中找原因,这是错误的。 |
|
|
|
| 陈: |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缺乏自我纠错机制,很容易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跑越远,全国尚未从“三年自然灾害”中恢复元气,又充满激情地冲入文化大革命的大动荡中,使党和人民经受空前的大浩劫。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三十多年了,可是至今仍然有人未能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大量有价值的个案作为反思的历史材料。您能否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亲身经历介绍一下? |
| 张: |
其实有价值的个案比比皆是,只不过早已散落在积尘发黄的旧书堆和喜新厌旧的脑海中。但是文革中的“极左”思潮阴魂不散,有时还会显现出来。文化大革命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每个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我当然也不例外。但是所经历的事太多太多,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谈起…… |
|
|
|
| 陈: |
那就按照时间顺序吧,因为这样便于您回忆和讲述。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形势还不明朗,可是几乎一夜之间便急转直下。您当为什么很快就陷入艰难的处境?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
| 张: |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就遭到从天而降的劫难。 |
|
|
|
| 陈: |
文化大革命竟然由挥舞棍棒皮带发展到动用真枪实弹,对此我感到匪夷所思。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经典理论在“文革”中能够得到部分实践,也许说明了“文革”实质上就是一场党内的夺权斗争。可悲的是自上而下波及广大无辜,多少人为此含冤九泉。听说您曾与死神擦肩而过,能否说说这段传奇故事? |
| 张: |
1967年夏天,江青发表关于“文攻武卫”、“砸烂公检法”的讲话后,“文化大革命”发展为“武化大革命”。部分农民持枪进城并强占土地,学校绿草如茵的运动场就这样变成了水稻田;一批批红卫兵冲击军区,抢枪、抢炮、占据点;各对立派间势不两立,冲突不断,如果本派有人被打死了,“战友”悲哀地播放毛主席语录歌曲:“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何等的“悲壮”?!对立派却幸灾乐祸,也播放起毛主席语录歌:“小小环球,有几只苍蝇碰壁,嗡嗡叫。”又是何等的“欢乐”!我就是在这种资产阶级派性十足的环境下艰难生活着,顽强地抗争着------ |
|
|
|
| 陈: |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性大串联构成当时交通线上一道最壮观的风景,我猜想您肯定也参与其中了吧,由于当时特殊的处境,您是否从大串联中收获一些特殊的体会? |
| 张: |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剥夺了乘车串联的权利,却“享受”到步行串联的“恩赐”。 |
| 陈: |
毛泽东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相当矛盾,一方面既让他们发挥所长为国家作贡献,另一方面又让他们远离专业和本职工作,从事最原始最落后的农业生产。文化大革命期间您也曾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就不是由自然科学改行为社会科学,而是从先进的工业文明退回到落后的农业文明,性质巨变,南辕北辙,在这种情况下您还能有所作为吗?对此又有什么深刻的体会? |
| 张: |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从一般的教员“荣升”为省级机关干部,“光荣”地参加了福建省直机关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
|
|
|
| 陈: |
我能理解您当时的苦衷。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期里,不仅知识分子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日子实在太短了,而且知识分子能够避免政治冲击的日子也不长,这应该与党在当时未能实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密切相关。解放后我国像鲁迅那样的自由知识分子基本上销声匿迹了,他们陆陆续续进了各种单位成了国家干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为“运动员”。古代国难当头时知识分子是“投笔从戎”,而现代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却“投笔从‘农’”,您能简单评价“文革”期间干部下放农村劳动的政策吗? |
| 张: |
干部下放到农村劳动,是文化大革命错误路线制造的时代产物,因为它是对“臭老九”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相的劳动改造,是误国殃民的举措,可以肯定地说指导思想和方向都是错的。 |
|
|
|
| 陈: |
文化大革命中期,虽然形势渐趋稳定,原有秩序渐次恢复,您所在的学校得以复办,而您也被调回学校参加复办工作,但是在以“政治挂帅”来“抓革命、促生产”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背景下,您是否又遭遇到“思想改造”的困惑? |
| 张: |
文革期间学校复办时,校领导组织我们学习周总理转毛主席圈阅的对解放后教育工作评价的文件,其中提到解放后教育战线被“黑线专政”,培养出来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校领导要我们统一认识,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
|
|
|
| 陈: |
您通过介绍自己在“文革”中亲身经历的重重磨难,多方面深层次揭露和批判“文革”的荒谬和残暴。现在要请您用一句话对文化大革命作个简短的总结,用以警醒后人不要重蹈覆辙。 |
| 张: |
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是一场大灾难,它不仅给中国的经济带来巨大损失,而且在政治上用“文攻武卫”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严重践踏,在思想上用形而上学对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价值观恣意歪曲,令人万分痛心地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极不光彩的一页。 |
|
|
|
| 陈: |
文化大革命还对我国的教育事业造成影响深远的巨大破坏,“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错误思想导致千千万万的青少年失去学习的机会,虽然“文革”结束后立即恢复高考,并且大力发展“电大”和“夜大”等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办学模式,可是只有少数肯吃苦敢拼搏的“幸运者”由此改变自己的命运,当时他们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听说您在“文革”后也是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彻底解决改行造成的历史后遗症,那时的您早就步入了中年,人们常说人到中年万事休,而您四十多岁还到厦门大学进修,要知道那可是在1984年,国内还未流行“终生学习”的口号和实践,您能否详细介绍当时的具体情况? |
| 张: |
在学校改教社会科学后整整过了二十四年,我突然陷入无法评职称的困境。“服从国家需要”改行后,我几十年如一日地提升专业水平,将勤补拙,靠自学和寒、暑假到省委党校进修,掌握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共党史》等四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授课的班级有中专、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三个层次,因课堂讲解深入浅出,生动具体,深受学生欢迎,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 |
|
|
|
| 陈: |
通过在“厦大”的进修,您终于“挤进那个圈子”,得到专家的肯定。我很想知道您在“厦大”进修期间,最难忘的事是什么? |
| 张: |
在厦门大学学习期间,最令我难忘的事是:1985年我在撰写《试论“两权适当分离”与经济体制改革》这篇论文时,遇到了许多理论前沿中有争议的难题,仔细整理后罗列下来,准备请教当时厦门大学党委书记、久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吴宣恭教授。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把问题寄到他的办公室,半个月后,我意外地接到他的一封简函,说他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回来后,才看到我提的问题,迟复为歉!并约我到他家详谈。我高兴极了。 |
|
|
|
| 陈: |
目前又一轮高中新课改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大力提倡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等先进理念,但是老师们纷纷抱怨当今绝大部分学生不仅没有各种新教法提倡的创新精神,而且没有传统教学方法奠定的扎实基础。另一方面,学生们也抱怨当今相当多的老师只会满堂灌,令人昏昏欲睡。可是数十年来您的教学效果在校内外反映都很好,请问有什么独到的经验? |
| 张: |
我认为教师首先必须为人师表,这是共性。而各门学科特点不同,教学方法也不相同。就从我所担负的马列主义理论课程来说,就有其独特的要求和特点。 |
|
|
|
| 陈: |
我国长期坚持实行计划生育的国策,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确实取得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在独生子女的教育方面却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其中的一些表现直接导致学校管理工作出现一个新难题,就是如何动员老师担任他们最害怕也最想逃避的职位——班主任,我发现许多评优和晋级标准都有规定教师必须担任若干年的班主任,这一定是无奈的制度选择。据我了解,高校基本上都是由年轻教师出任辅导员,而您从青年到中年多次担任班主任,并因工作成绩显著多次荣获表彰,我想您一定非常愿意将所积累的经验和体会告诉后人,能否简单地作个总结? |
| 张: |
从1960年到1989年,我担任过五个班级的班主任工作,曾被评为优秀班主任。我的体会是:要做好班主任工作,对班级学生既要有爱心、真心、诚心和耐心,又要严格要求;要发挥他们的特长,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切忌居高临下,处处以领导者自居,不能平等地对待学生,更不能偏爱学生。只要严格要求自己,为人师表,把学生当成自己的知心朋友,各项工作一丝不苟,及时发现和妥善解决矛盾,就一定会得到学生的支持,把班主任工作搞好。 |
|
|
|
| 陈: |
我知道您不仅是个优秀的班主任,而且也是一个出色的党务工作者。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背景下,党务工作处在比较边缘的位置,既难以开展工作,又不容易出政绩。可是您曾被评为校优秀党务工作者,能谈谈你入党的经过和党务工作的情况吗? |
| 张: |
我的入党过程是漫长和曲折的。我1956年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因有海外关系,没有列入建党对象。但入党是我坚定的信念和热切的渴望,是对新政治生命的强烈追求。为此,数十年间我从未动摇和灰心,不同时期先后递交了六次申请书。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个月,经过二十二年的漫长等待和党的长期考察,党组织终于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
|
|
|
| 陈: |
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常常“文人相轻”,而各种学术团体大多数是属于松散的社团组织,许多工作难以顺利开展。您曾担任过全国和福建省学术团体的负责人,有什么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呢? |
| 张: |
我曾有幸担任过中国职教学会政教委员会副理事长和福建省职教学会政教委员会理事长等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在这期间,我提出做好学术团体工作中应遵循的原则是:大家的事情大家办,我们办事为大家以及权力和义务的统一。 |
|
|
|
| 陈: |
通过对自己丰富经历的简短回顾和对自己丰富经验的简短总结,此时此刻您一定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呼之欲出,因此我恳请您打开激情的闸阀,展开心灵的翅膀,尽情抒发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吧。 |
| 张: |
蓦然回首,我已走过七十年的漫漫人生路,在经历了“反右派斗争”、“拔白旗插红旗”、“高举三面红旗”、“三年自然灾害”、“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逆流的磨砺之后,欣喜地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灿烂阳光;在“服从国家需要”的名义下违心改行后,经过短暂的调整,我愉快地从事长达四十三年的“传道授业”的神圣事业,依靠自己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一定的成绩,多次荣获省级、校级的各种表彰,得到社会方方面面充分的肯定。一年年坚守在传承知识的黑板前,注视着不断变换的一张张年轻面孔,我不敢自夸“桃李满天下”,但是我能自豪地说“桃李遍福建”。 |
|
2007年10月16日于福州 |
|
<<芙蓉网>>按:<<人物掠影>> 栏目旨在与大家一起分享校友们奋斗的艰辛历程和生活体验,它将记载著国光人奋勇拼搏的精神和不懈追求的足迹。希望校友们踊跃推荐,无论是对话、采访、个人简介等体裁我们都欢迎。请把稿件及照片(包括个人照)电邮到:info@fu-rong.cn 谢谢! |